海口心灵氧吧

写作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发布时间:2012-12-19 22:13 类别:职场心理
心理导读:麦克尤恩笔下的军情五处墨守成规,职员全是资本家式的傲慢中年男人;档案柜都按日期排号,而不使用隐形墨水。他说,他对军情五处的内部制度和这些制度如何滋长成为奇怪的逻辑感兴趣。 ---www.tsps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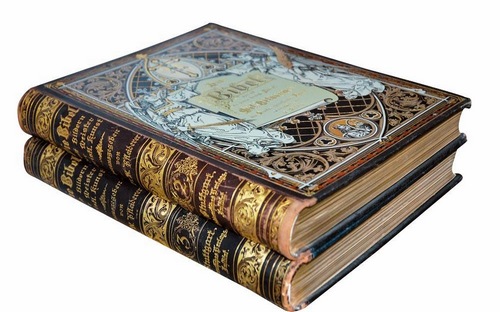
写作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在萨塞克斯大学第三年快要结束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有点不情愿地走进了职业指导办公室。他一心想成为作家,但是他又想,是否有什么办法使自己的理想兼顾父母的期望,找到一份令他们满意的体面工作:“我读过劳伦斯(TE Lawrence)的《七根智慧之柱》,我曾想着当一位阿拉伯学者型外交官,可以在晚上穿着晚礼服,第二天晚上又戴着阿拉伯人头巾。”职业指导办公室给了我一个小册子。“小册子后面是个表格,表格有两列,一列是你的年龄,一直到65岁。另一列是你在各个年龄段的期望收入。我看着表格,顿时我害怕极了。我的生命就在这里了。我要在接下去的35年里按照这个表格完成我的工作了。”成为一位有抱负的作家并骑着骆驼穿越茫茫戈壁的梦想顿时变成了泡影。
幸好那是七十年代初期,人们信仰活着就是一种幸福。这是实话!“我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麦克尤恩说这话时,还扬起了他热情的笑脸。“即使没有工作,成为一位全职作家,你的生活也不那么艰难。我在南伦敦租了一套很大的公寓,租金每周只要3英傍。偶尔我还会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点评论,或为《广播时代》写几篇稿子。即使这样,我也能轻松地支付房租,我还能买些书,每周还可以去一趟自助洗衣店。不必准备家电这些必须品,我只买了个音箱。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多清苦,听起来有点儿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每年只花700英傍过生活。”
但是发生意外状况怎么办?成堆的垃圾、停电、或死了尸体都没人掩埋?“噢,这些意外我根本就不担心。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我也不怕冒险。我那时真是没一刻清闲,兴奋极了,还有点儿粗心大意。我还记得我读过丹尼尔·笛福的《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我喜欢城市里来点儿混乱。书里大概有这么句话,‘我们向伦敦的北部走去,因为不想太阳直面我们。’我那时想:这才是真正的自由。‘随它便吧’我总是有这个感觉。”
然后是短暂的沉默。他可能在想,那个不安分的年代是如何结束的,而我却试图找到七十年代头发垂到粗棉布领子的麦克尤恩,和二十一世纪穿着雅致碎白亚麻衬衫的麦克尤恩的相似之处。他现在的生活可能单纯多了吧,因为他会这样告诉我:“现在你有了孩子,你有了抵押品,你就要工作;你被锁定在人类文明计划当中,你希望这项计划成功并让它发光发热。”对于我来说,一段跳脱性思想也是必须的。当我被告知我要在麦克尤恩出版社(兰登书屋)的会议室访问他时,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想要看看,麦克尤恩其中一处非常有名又温馨的家是什么样子的(最好是精致的费兹洛维亚连排房,麦克尤恩的小说《周六》里的主角外科医生亨利·佩罗恩的家就是以此处为背景)。但是,现在我觉得一切还好。麦克尤恩很像EL·詹姆斯,她的《五十度灰》系列小说正在热卖;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克尤恩休息室的椅子就像是国王的宝座,虽然他不太舒适地坐在上面——椅子总是转动,他不得不把膝盖蜷曲着朝向说话人的方向。所以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再看到他进洗衣店,或者观看庸俗的电视节目《Only Way is Essex》。
七十年代,又是七十年代。麦克尤恩的新小说《甜齿》(Sweet Tooth)的时代背景就设在七十年代。我不想透露过多故事情节,理由很简单,首先小说就是那种罗杰·艾克罗伊德似的侦探小说?,再有成为剧透破坏读书兴致实在不好。以下便是简单的故事梗概:塞琳娜·弗罗姆刚刚从剑桥毕业并被招募到军情五处。非常喜欢读小说的塞琳娜被安排参与一项冷战宣传计划,代号为甜齿。这项计划秘密地用政府资金资助那些对西方国家有好感的知识份子,其中的一个目标人物就是作家汤姆·哈利。塞琳娜先是爱上了作家的小说,然后又爱上了作家。显然,她不是一个称职的间谍。看来,真实世界和她同样身份的斯黛拉·瑞米特一定要请她吃顿早餐好好谈谈了(甜齿还顺便提到了她的一位很有抱负的女性同事米莉·特瑞姆?)。
这部奇特又很迷离的作品——一部间谍小说却没有太多暴虐的故事元素——是如何开始创的?是先有军情五处还是七十年代?“这不太好说,”麦克尤恩说道。“我是不知不觉有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杂志《偶遇》事件感兴趣[1967年,《偶遇》文学杂志主编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辞职,据称杂志社接受了美国中情秘密捐助],我就想这件事儿能否发生在我身上;写完背景设在六十年代的《在切瑟尔海滩上》(On Chesil Beach),我又想,早晚我要写一写七十年代的英格兰。这就是《甜齿》的两条主线。最后,我拿起了我的绿色笔记本,让塞琳娜开始讲话——虽然这样做有点儿违背我的意愿。”为什么?“因为我对使用第一人称讲故事有偏见。理由很多:这种方式叙述故事太简单了;这只是一种腹语术,作者可以规避性格化背后的粗鄙风格;可以任意使用陈词滥调。”
麦克尤恩笔下的军情五处墨守成规,职员全是资本家式的傲慢中年男人;档案柜都按日期排号,而不使用隐形墨水。他说,他对军情五处的内部制度和这些制度如何滋长成为奇怪的逻辑感兴趣。“冷战期间的文化冷战相当特别,尤其是美国中情局投入上百万美元支持一些很有价值的文化活动——如1950年的无调性音乐节。中情局想要说服欧洲左翼知识份子,让他们相信西方制度是最好的社会制度,美国也不是只追求物质利益的无脑者。当你想到苏联专制政府制造出的骇人事件,你会想:为什么不接受捐赠呢?但是你仍然会想:他们为什么要秘密的做此事呢?为什么美国政府不使用全国艺术基金会等这种组织来向文学界捐赠呢?他们从未想过这种秘密的捐赠是不需要的吗?”
然而,小说中的主角汤姆·哈利一旦出现,麦克尤恩对军情五处的关注就会有些动摇,这可能是因为麦克尤恩和汤姆·哈利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哈利在萨塞克斯大学当老师;他的书由汤姆·马斯库勒出版,马斯库勒正是麦克尤恩第一部作品的编辑;他把他的第一本小说读给马丁·艾米斯( Martin Amis)听,艾斯斯恰好是麦克尤恩的朋友;书中主人公撰写的两个故事其实是他的创造者顺手从其旧书稿中攫取的。“是的,”麦克尤恩说。“说到点子上了。这部小说是一本失声又失真的个人自传。当然,很不幸,现实中从未有个漂亮的女人走进我的房间并给我一笔津贴。”
那么他在小说中到底说了什么?事实和虚构的结合,贯穿小说中多处表里不一的故事,再结合激情描述阅读和写作,至少在我看来,《甜齿》在思考,小说家可谓是个狡猾且冷酷的“小偷”;难道主人公汤姆·哈利说的还不够多吗?“是的,他说的够多了。汤姆提到写小说时这个残忍的过程是必须的——这也让塞琳娜害怕,她担心自己也会成为他的小说素材。”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曾说过所有作家的心中都有“永不消融的一块冰”。他也是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菲利普·罗斯好多年前就告诉我,写作时要当你的父母全死了,那时他很留意我这个年轻作家。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一直这样做。现在回想起来,我却感到非常恐怖,特别是我的父亲,他好像被撕裂了一样,他既极度骄傲我的书可以书版,同时又对书中的内容感到害怕。所以最后我只得狠下心来保持一种漠然。但是我却做不来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小说《赫尔佐格》时的所为,也不能像菲利普·罗斯或汉尼夫·库雷什(Hanif Kureishi)等一样把自己的前妻也写在书里。我真的做不到。”他又想了想说,“我心中的那块冰有点……消融了。”
伊恩·麦克尤恩的父亲大卫是个军人,他出生于苏格兰工人家庭,后经过努力成为一名军官。麦克尤恩在奥尔德肖特市出生,然后最先生活在德国,接着是利比亚,在11岁时又被送到(英国)萨福克郡州立寄宿学校生活。麦克尤恩说过这段时光非常黯淡:“我浑浑噩噩地在那度过了四、五年。”另一方面,麦克尤恩这段住校生活经历也派上了用场。2005年,他和环境组织好望角告别(Cape Farewell )来到北极圈斯瓦尔巴特群岛旅行,这次旅行是他的前一部小说《追日》的灵感来源。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装备在衣帽间里狼藉一片,他的东西早已整理好并放在了床底下。?
在苏塞克斯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位后,他又到东安格利亚大学修读硕士学位,他的导师便是安吉斯·威尔逊(Angus Wilson)和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1974年,麦克尤恩搬到伦敦居住,从这时起他就成为伦敦文学圈的一部分,这个文学圈以伊恩·汉弥尔顿(Ian Hamilton和他的导师威匀尔逊都出现在《甜齿》中)的《新评论》杂志和位于伦敦苏豪广场的希腊街赫丘利斯之柱酒吧为中心。同样在这段时期,他和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和弗斯多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结下了最深厚的友谊。
去年希钦斯患癌症去世。没有希钦斯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噢,不。麦克尤恩表情如此凝重,而且惨白。我真希望我没问这个问题。“简直是……一片荒芜,而且空洞。他是我们当中拥抱所有文学形式的那一个;光阴荏苒,我相信后人并不会把他和他在伊拉克战争的独特立场相联系。人们只会想起他评论作家切斯特顿、吉卜林、沃德豪斯的那些优秀文章。人们只会念着他的文学品味和他机智的谈吐。我非常想念他,马丁和我会在后希钦斯时代的荒凉沙漠中互相审视。”
希钦斯如何能和你们一直保持友谊?文人相轻,文学界总是充斥着恶言和妒语,还有争吵更是最普遍现象。“我们在没成名前就已经相熟;而且我们也不是明星,时不时就要在一起开个派队。” 麦克尤恩还说,小说创作并不是跑步比赛,不需要你争我夺;每个人都有足够空间创作出优秀作品。“或者我们太老了,无所谓嫉妒谁。对身份的焦虑感也已经消失。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和朱利安在一起吃饭是一件愉快的事儿。”
但是,如果你们当中的某个人事业不顺走了下坡路,又或进入了名气稍逊的圈子,那该怎么办?“是的,可能总会有些改变。可能最后这只是一个自我选择社交圈的过程。谁总会膩在赫丘利斯之柱酒吧?只有那些心怀激情想写书的人才在那里。我们都下定决心成为作家。我们并不会使用‘激情’这个词,但是我们会用行动表达激情。写作是我们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情。”
麦克尤恩要比艾米斯晚成名。他早期的作品调子阴郁,常常以死亡为主题——想想那些乱伦、谋杀、和商店的人体模型做爱的故事情节。这些小说都获得了赞誉,也为他赢得了大批忠实读者。但是,这些作品在我印象中好像都不是畅销书(他的第一部小说在1975年发表)。然后在1998年,他的小说《阿姆斯特丹》获得布克文学奖。九年之后即2001年,小说《赎罪》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奥斯卡奖。从这时起,他的作品总以两倍、甚至三倍的销售稳增。成功是否可以激发他的创造力?
“当然,成功与否的确有些不同,”他说。“我总会随心所欲做我想做的事儿,结果当我关上门,拔掉电话线时,我依然焦虑如何把眼前的事儿做好。”当然他同样会图增新的烦恼。“你总是担心,迟早有一天你真的不能再写作了;有一天你会才思枯竭;有一天你面临着总是重复自己的危险。所有60多岁的作家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什么时侯你应该停止写作?你只能不了了之地写些孱弱的中篇小说凑数?在沉默与无人之地努力克服困难时,是否成功也就没什么特别之处。”他还热心地提醒我,小说《赎罪》完全是个异类。“如此受人追捧只有这么一次。最近的两部作品并没有赢得人们的喜爱,即使有人喜欢它也仅是小众而已。坦白地说,《追日》在美国不招人待见,恶评之声络绎不绝。”
有些不太对劲儿。即使麦克尤恩给我浇了一盆冷水,我也会这么想。在我们这些外人眼里,麦克尤恩生活充实,而且又有事业心,可以说他的生活非常快乐,虽然“快乐”这个词总不能和作家联系在一起。麦克尤恩足够快乐,他一定都厌烦了!他笑了。“当然,你也可以这么想。”然后他又说:“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第二段婚姻很美满[他的妻子是记者安娜·麦卡菲,她在一次访问中认识了麦克尤恩]。我们都得学会如何做到更好……儿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他和前妻佩妮·艾琳在1995年离婚并育有两子]。我想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父亲并不是无所不能时,这一定很凄凉。但是我喜欢老早给他们展现人生的各种故事其及情节。”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分子生物学家,另一个在公共关系科工作。
麦克尤恩对我说,你不一定能掌控生活的节奏。但是我仍然能从他的脸上读到满足感,虽然他的父母(现在已经去世)受到了人们的指责。我想,这种内心的平静总是和他的努力有关。麦克尤恩父母的婚姻遭遇困境,这几乎是因为一个保守多年的秘密:2007年,麦克尤恩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同胞哥哥。哥哥现在名叫尉戴夫·夏普,是他的母亲露丝在和其第一任丈夫在婚姻续存期间生的孩子(她和第一任丈夫欧内斯特·沃特有两个孩子;她和麦克尤恩的父亲大卫·麦克尤恩的孩子在1942年出生;1944年沃特在战场中负伤身亡)。然而孩子的亲生父亲却在《Reading Mercury》报纸上登出广告遗弃了这个孩子:“需领养者,一个月男婴;完全放弃抚养权。”
“广告一定是我父亲写的,”麦克尤恩说。“‘完全放弃抚养权’——是个军官的口气。”当得知父母的秘密时,他是否受到煎熬?“是的,我真想和他们脱离关系,并对他们说,‘面对这一切;解决这些困难,然后使自己充盈快乐。’我最大的遗憾是父母一生都没见过大卫,可能是大卫向他们保证过,他的生活并不遭。大卫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时侯我的养父母很爱我。’他去看望我母亲时,母亲已经患病失去了记忆。如果他能早来一年的话……”
这真是个伤心的故事,麦克尤恩的母亲最后还是和她的情人结婚了,他们本可以再共同抚养这个孩子。“是的,他们为了自己而隐藏了这个秘密。可能我的父亲也是这么想的,我总听见他说‘木已成舟’。也是,在我父母那个年代……直到60年之后人们才敢谈论这种话题。”
他哥哥(是个泥瓦匠)的出现是否使他的生命感到知足?我想一定是的。即使他们不是最好的朋友,一束耀眼的光芒同样会在另一处阴暗之处闪烁。麦克尤恩不这么想。“我的生命更加丰富了,”他静静地说道。“确实是这样的。”
麦克尤恩的名望使他的小说《甜齿》在没有出版之前就引起人们的轩然大波;布克奖评委也粗暴地没让他的这部作品入围。“噢,现在我对布克奖已经不感冒了,”他这样说。对于一位已经获得布克奖的作家,说这句话时显然得很轻松。“我认为,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像普利策那样的奖项,英国至今还缺少这样的大型比赛。这就像110米冲刺比赛,总给人一瞬间粗鄙的感觉。”至于对这本书的各种评论,他并没有读。是否他认为,或像很多人断言的那样,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出版业的结束和小说创作的慢慢消亡?“我们总是渴望谈论、思索他人的一言一行,我认为除此之外,无它形式可表达我们最真实的内心。”
屏幕或纸张并不重要。另外,麦克尤恩刚刚乔迁搬家——是的,享利医生的家已经出售,新家被安置在(伦敦中部)布鲁姆斯伯里的一幢公寓和格洛斯特郡的一处宅邸。他花了好几天时间把装箱打包的藏书从盒子里搬出来。“是的,把它们放在书架上,宛如重新讲叙你依旧存在的故事,”他说。“这些发脆、泛黄的平装书全是我在17岁时买的。我不会再重读它们,但我也不会把它们扔掉。”他环抱了一下自己,尽量让我看起来他有些神经质。“我希望它们围绕在我身边,再好的电子书也不能给我这种感觉。”
(文/心灵花园 www.psy0898.com)
译注:
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26年创作的侦探小说《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里的人物。
Stella Rimington,英国作家,她从1992到1996担任过英国军情五处的局长,她也是第一位任职于军情五处的女性局长。
小说中的这个虚构人物Millie Trimingham,在现实生活中指的是后来担任军情五处局长的Stella Rimington。注意,在这里麦克尤恩故意使两个人名的发音节奏相似。
麦克尤恩在一次访问中谈到了这次旅行:
我们整个晚上都在谈论气侯问题,讨论世界如此需要我们对文化和行为方式做个彻底改变。同时我们隔壁的衣帽间也混乱不堪,所有的户外服装和雪上摩托车等都堆在那里。我们生活中这种自造的混乱和我们生命中的抱负、理想存在巨大反差,这正是一种很幽默的表现主题的方式。
下一篇:心理治疗的实质是爱的传递 上一篇:性格分析师的敏锐观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