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心灵氧吧

心理学堂:死亡恐惧与害怕
发布时间:2013-03-31 20:17 类别:心理学堂
心理导读::我们越不熟悉的东西与环境,我们就越容易产生担心与害怕的心理境况;而我们越熟悉的事物与地方,我们也就越能安心和无惧。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我们最不熟悉、最无知的事物的话,那么它就是“死”了。 ---www.tsps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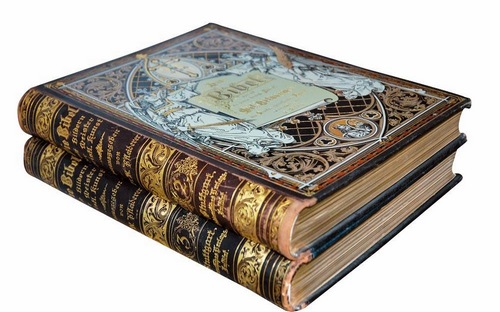
心理学堂:死亡恐惧与害怕
对于“死”,世上鲜有人不害怕的,但若近一步追问,我们究竟怕的是什么?恐惧的是什么?许多人可能张口结舌,无法给出确切地怕什么恐惧什么的答案;有些人也许能说点什么,但与别人的回答又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这就使此一问题像雾中看花,颇有些朴朔迷离起来。不过,要消解我们怕死的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我们究竟怕的是什么?
一、“死”是何物?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越不熟悉的东西与环境,我们就越容易产生担心与害怕的心理境况;而我们越熟悉的事物与地方,我们也就越能安心和无惧。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我们最不熟悉、最无知的事物的话,那么它就是“死”了。所以,人类最害怕的事物不是别的什么,也就是“死”这个东西了。
台湾成功大学副教授赵可式博士问临终病人,为何恐惧“死”?其中一个病人答道:“毕竟我没有死过,我不知道死亡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什么滋味及景象?死后会到那里去?全都不知道”。所以,人们对死亡的害怕,第一个方面就是“未知的恐惧”。(参见《台湾癌症末期病患对善终意义的体认》,《安宁疗护》1996年第5期)
人们对“死”的未知,实际上正显示出“死亡”本质的一面,即:活着的人是不可能经验“死”的。人的意识、观念、认知的领域已经因我们的感官与思维而划定了确定的范围,人是无法越出其一步去知道更多东西的;而人之“死”,是人的所有生理器官的衰竭与停止,如此的话,我们又如何能知“死”?所以,可以这样说,人都是活人,“死”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没有任何感觉与知觉,这就是古希腊哲人的看法。中国古代的哲人也讲“生不知死,死不知生”,又何必怕死?又焉能怕死?试想一下,我们什么都不知晓了,拿什么去害怕呀?!“恐惧”是一种人的心理活动,它带给人一种无助的、担心的、焦灼的痛苦,其产生的基础是我们活着的机体;而“死亡”一降临,活的机体已不复存在,我们又焉能“恐惧”?
所以,有的思想家指出,人不可能怕“死”本身,那是怕不了的;而是怕“死”的观念,是人生前对“死”的观念的害怕。因此,人们怕死,实质上不是对一种实存事物的怕,而是对抽象的观念的害怕,由此,人们也许可以获得一种消解死亡恐惧的方式:我活着时,死亡未来临,即便临终前的刹那,我们还是活人,不知“死”,又何必怕“死”?而当我死去时,我无知无觉,我已经不能怕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供自己产生害怕情绪的东西,可见,“死”与我是毫不相干的。
人们可以由未知而对“死”产生恐惧,同理,也可以由“未知”而导致对死的不恐惧,崐关键在人们要理解“害怕”、“焦虑”、“恐惧”等一切心理情绪均必依赖于我们活着的机体这个事实,人类不可能经验“死”的实存,只能在观念中想象“死”这个概念,所以,引起我们害怕的并不是实存的“死”,而是观念的“死”,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怕死呢?
但是,以不知“死”,故而不必怕死的思想原则来安慰人,恐怕只能使部分人信服,另一种安抚方式是告诉人们应该具备正确的生命观。
一个人若仅仅从个我生命的视角来观察,必会觉察生命由形成、孕育、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等阶段组构而成;而死亡意味着生命的毁灭,因此,希望长生不老、免于生命的止息成了人类永恒之梦。当然,更多的人则去养生锻炼,希望活得长久一些,健康一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跃出个我生命的限囿,从生命整体的高度来看一看,这时我们就能发现:所谓生命的毁灭仅仅是个体生命的消解,而决不是整体生命的完结。恰恰相反,个体生命的死亡正是整体生命创生的一种形式。所以,与其说“死”是生命的终结,毋宁说“死”是生命再生的中介。所以,我们每个人虽然都会“死”,都必“死”,但一当死去,我们便参予入整体宇宙生命的创生过程中去了。我们身体的分解,实使更多的生命在繁殖;我们的生命信息仍然在世间保存;我们的“死”实形成了滚滚不息生命洪流中的一朵美丽永恒的浪花。从这种视野去体会,我们就能发现,“死”又是可知晓的,它就是生命的特殊转化形式,自宇宙有生命现象,出现生命个体以来,无数的生命物诞生了,又死去了,又诞生了,又死去了,它们都随顺着自然大化的安排;为何唯独我们人类,却对“死”万分悲哀与恐惧?为何我们总是企图要改变必死的命运?为什么我们人老是在面临死时达不到心安?这岂非人类的最大悲哀?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大其心”的人生方法,跃出个我的躯壳与经验,立于宇宙之整体来体会生命的本质;并从自我之死的执着中跃升出来,由此,便可以“死”亦是一种“生”来获得心灵的解脱,并察觉到他人之“生”又何尝不是自我之“生”的一种状态?如此,又何有“死”?无“死”,又何必要怕“死”、拒“死”、不安心于“死”呢?
以上的观念可称之为消解死亡恐惧的生命体验法,其关键在突破个我生命的限囿,把自我之小生命与他人之生命,乃至宇宙的大生命加以沟通并融汇为一、合成一体,从而体会到这样的真理:生命具有共通性,“死”不是毁灭,而是新生、再生、共生──从而永生。
当然,也许消解人类死亡恐惧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宗教一般都源于人类的苦难,尤其是必死的悲惨命运。因此,大的宗教都发展出独特的死亡解释模式和安抚死亡痛苦的方法。不过,对中国人而言,宗教消解死亡恐惧的方式非“不知也”,而实在是“难为也”。因为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宗教信仰完全缺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没有提供这种可能与基础;而即便宣称有某种宗教信仰者,其信教也只有部分人是发内心的虔诚信仰,更多的人则是抱着功利态度,从众心理去信教,从而大大减损了宗教在安抚人们对死亡恐惧方面的功能。所以,一个人要真想从宗教资源中获得消除害怕死亡的观念,就必须要具备真诚的信仰,否则是难以奏效的。
周长旗修女在《天主教徒如何做灵性照顾》(参见《安宁疗护》1997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当一个天主教徒面临人生的终点时,要“用祈祷、用圣事、用实际的行动‘爱’,加上病患者自己的祈祷领受和还爱(对天主的还爱)”,那死者就一定能获得解脱和善终。周修女指出:“祈祷是什么呢?祈祷是内心的奋发之情,是向上苍的淳朴凝视;是困苦中或欢乐中感恩报爱的颂谢声。祈祷是举心向往天主,或者向天主求适合的思想,病患因自己的热心祈祷可获得力量和心灵的平安。”
“用圣事”包括“忏悔圣事”、“傅油圣事”和“圣体圣事”三项。周修女提出:“人在患病时,需要天主的特别帮助,使他在痛苦中不致失望。令他感到天主的爱,更能依赖天主获得力量,以抵抗对死亡的畏惧。……举行傅油圣事的必要仪式是:神父在病人的前额和双手傅持圣油,同时以礼仪祷词,求使病人获得这圣事的特别恩典。病人傅油圣事的特别恩宠具有以下效果:病人为自己以及整个教会的益处,与基督的苦难结合,带来安慰、平安和勇气,好能以基督徒的精神,忍受疾病的痛苦。如病人未能藉忏悔圣事而蒙赦免的话,他的罪过可因此得宽赦;如果有助于其灵魂的得救,可恢复病人的健康,准备逾越此世,进到永生。”
“圣体圣事”,是与天主生命相通、与天主子民共融合一的标记。人们吃下象征基督身体与鲜血的饼酒,意味着与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连同他的一切全部合为一体。周修女写崐道:“领圣体的效果:是与耶稣基督亲密结果,可获得灵性生命的滋养,并与罪恶分离,是灵魂的处方,有治疗作用,是长生的良药,抗除死亡的解毒剂,使我们永远活在耶稣基督内的食粮。教会给予那些即将离世的人圣体,作为天路行粮。在回归天父的这一刻所领受的基督圣体,含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性。基督的圣体是永生的根源和复活的德能,在此圣体圣事是基督死亡和复活的圣事,是由死亡通往生命,从现世迈向天父的圣事”。
天主教为临终者展开的这一整套操作,均可视为是让信徒使自我的生命与生命整体──耶稣基督相沟通、融合、成为一体的努力。“祈祷”与“忏悔”,是人们在天主面前坦陈生命的全过程,以消解人生的罪过,求得宽恕,这是一个生命体的全面开放。而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或多或少是闭锁住心灵的,使人生中许多悔恨之事在心灵深处扭结,形成所谓“心病”,在人临终时尤其会造成悔恨、焦灼等深度的痛苦,通过“祈祷”与“忏悔”,我们在天主面前坦陈全部心灵隐密,从而舒解了内心的疙瘩,获得了解脱。而“傅油圣事”与“圣体圣事”,则是把自我之小生命投入无限之大生命之中,由此人们对或迟或早必降临之“死”便可抱顺应的态度而毫无痛苦。因为通过分享生命整体──象征着耶稣基督身体和鲜血的饼酒,我们的现世生命完全地与无限的生命和合为一了,于是,我们达到了善终,实现了永生。
周修女运用天主教这一整体灵性照顾的方式对一位临终病人进行了安抚,这位病人对她说:“修女!我到天上去后,一定会保佑你。《野地的花》这首歌告诉我,天父都会照顾野地的花和天空飞鸟,我的孩子阿弟亚他一定也会照顾。”周修女写道:“最后她是以这首歌放下了心。她全心信赖天父自会照顾,在一切都准备妥当(我们为她做了傅油圣事)后,平静微笑地跟着耶稣到天乡去了。真美的善终。”
从此一实例可以知晓:个体生命与整体生命的融合,实际上也就是“生”与“死”的沟通,把原来万分恐惧之“死”视为个我生命投向无限生命的桥梁,于是,“死”就消褪了一切令人害怕痛苦的性质,相反,它透显出静谧的安息的温暖,使人心安无惧地投入它的怀抱。
“一无所有”
在中国大陆,有一首风靡大众的摇滚乐歌曲《一无所有》,词曲及演唱均是被誉为大陆“摇滚王”的崔健,其词有三段: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
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
噢,你这就跟我走。
你这就跟我走。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首歌词的大意简单明了:一个热恋的男人,从姑娘的眼中读出了对自己的怜悯──“一无所有”,但他决心以自己的远大追求和心灵自由去感染她、溶化她。姑娘的手在颤抖、泪水直流,她的心很矛盾:是爱情至上,义无反顾地跟他走呢?还是理智至上,因其“一无所有”而拒绝他?这个男人非常自信:姑娘爱我也许就在我的一无所有!可现实生活中,又真有美丽的小姐跟着“一无所有”者走吗?歌曲结尾一方面毫无把握地问“你何时跟我走”?另一方面则半是恳求、半是绝望地吟咏“跟我走”、“你这就跟我走”。
1997年底笔者曾在巨大的江西体育馆亲眼目睹、亲耳聆听了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在震耳欲聋的24组大音响播出的轰鸣乐曲声中,崔健及他的“红旗下的蛋乐队”边唱边扭,而台下简直就是沸腾的大热锅,数千人同声高歌,声音大有冲破钢骨造成的大厅、直奔云霄之势。我的心灵深深地震动了,众人全身心地投入唱这首歌,背后必定隐藏着某种共通的心态和秘密,必定有一种相同的文化情结,尤其是共通的人生境遇包含在内。
二、它们是什么呢?
仔细看看歌词,就不难发现这个共同的东西:现代社会中的人痛感自己“一无所有”。
此“一无所有”,并非是实存的状态,因为人们不可能真的“一无所有”;而纯粹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观的虚幻感觉。如果从物的拥有来看,人生事件的丰富程度而言,现代人拥有的比之传统人(古代人)要多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可现代人在主观感受上还是觉得拥有的太少太少,乃至于“一无所有”。为什么会这样呢?
美国心理学家斯塔西·亚当斯在60年代便提出了著名的“公平理论”,该学说指出:一个人对其所得的报酬是否满意不是看其绝对值,而是进行社会的横向比较和历史的纵向比较,看相对值。比如把自己的报酬与贡献的比值与他人的比值相比,若发现自己努力所获得的报酬高于别人作同样努力所得到的报酬,便产生满足感,反之则不满足。
所以,一个人是否感觉到自己“拥有”,并不在他实际上真的拥有了多少东西,而在与他人进行的比较中,觉察自己拥有的多少。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自己拥有的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比自己拥有的多的多的人,于是现代人常常产生占有的太少的感觉、乃至于“一无所有”的强烈感叹。不仅如此,相对于我们已经拥有的那些数量有限的物品而言,现代科技每日每时每刻发明、创造、生产出的东西简直就是无穷之多,相形之下,我们拥有的是多么的少,怎不是“一无所有”?况且还有那“信息爆炸”,无穷多的书籍、光碟都使我们自觉到自己所知是多么的少和贫乏,这是精神世界的“一无所有”。
可怜的人,在“一无所有”的存在感受和心理愿欲的驱策下,于茫茫人生大海中苦苦奋斗、拼搏,去企及那似乎永远达不到的“拥有”后的满足。
可见,人生过程中,人们很难觉察到自己实际上拥有很多,仅仅是感觉上的“一无所有”,就给人造成人生极大的痛苦;顺延着想像一下我们每个人的“死”吧!“死”不是虚幻的而是真真切切的“一无所有”,即完全丧失,人世间我们拥有、占用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每个人都明了的人生真谛,由此所引发的痛苦当然成为人们临终前最大的恐惧之一。
赵可式博士经过实证性调查研究,指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还深刻地表现在:“失落的恐惧”。她写道:“许多位病人是由于舍不得亲人,舍不下世间所拥有而恐惧。有一位病人说:‘我这些年来好辛苦赚钱,现在有一千万,却没办法享受,好不甘心哪!’死亡将人在世间所依恋的人、事、物都割断,是一种很深的‘痛’。”所以,赵博士说:“小孩面对死亡,有时候反而比大人容易,这与我们的想象相反。这是因为小孩子没有那么多可失落的。因此,人拥有的越多,失落的也越多,造成的恐惧也越大。”
人在生存过程中,拥有的再多也会觉得不多,以至感叹“一无所有”;但一俟面对即将、死亡的命运时,则又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拥有得很多很多,因为,此刻的人再也不横向去比较──与那些比自己拥有的多的人比;而是在纵向比较──与自己死后真正的“一无所有”来比,于是,人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来确实拥有很多,惜乎不能享受和花费,如此怎不使人万分悲伤和痛苦?
生前拥有却觉得“一无所有”;死时没有才察觉拥有多多,如此生死观既陷人生于疲惫不堪的焦灼之中,又使人临死前万般割舍不下,生与死皆痛苦,可见错莫大焉。
现代人由于受科学思维之影响,成天刻意于区分:首先把己与物分开,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自然宇宙间的一切均应该为我所用,为我所消耗,于是肆意于攫取自取资源,毫无顾忌地破坏生态环境。其次,则把我与他分别开来,认为我的与你的不同,我的才是真正的拥有,可以随意支配,你的则不是我的,只有挖苦心思去“搞”过来归己所有。于是乎,人与人之间陷于勾心斗角,集团与集团之间拼个你死我活,乃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兵戎相见,杀得尸横遍野、鲜血成河。再次,则是把己拥有的东西做数量与质量的区分,以为拥有的越多越好,价值越大越好。于是乎,成天奔命于占有,无所不用其极者则沦为小偷、强盗、杀人犯,等等,由此上演出一幕幕丧尽天良的人间悲剧。
可见,以生观生,仅仅立于人生前关注自己的生活,由厚己生作为终极的人生目标,极易于陷入巧取豪夺,无一刻止息的人生大拼搏之中。整个社会的人皆持这样的人生观,必使社会陷入争抢拼斗的混乱状态;整个国家与民族皆持这样的人生观,必走向惨烈的战争;更不用说此一过程带来多大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大破坏了。
所以,人们要试着学会二种人生观:一种是摒弃分离、区别、割裂的思考模式,以统一、有机、合和的观念为基础建构新的人生观。看到我是人,他也是人,人与人之间不应刻意地区分,而要相互沟通;我拥有的亦可给别人分享。人人作如是观,则社会必充满着和谐与温馨,杜绝争斗与相残。
中国古代有一个“楚王遗弓”的故事(参见《公子龙子·迹府》),说的是有一次楚王带着他心爱的“忘归”良箭在云梦之地打猎,不小心遗失了一张名叫“繁弱”的良弓。手下人十分着急,纷纷请求着要去找回来。但见楚王慢悠悠地说:
“不必了,我是在楚遗失的良弓,必定是楚国人得到它,总归为楚所用,又何必去寻?”
孔子听说此事后,评论说:“看来楚王有仁义之心,但远不够完全,只知有利于楚,而不知道有利于天下。实际上,普天下之物,人所失必又被人所得,又何必单单偏爱于楚呢?”
楚王掉了宝弓,完全不着急,认为是在楚地掉的,自然是楚人得到,所以不必去找回来。这是把自己与一国臣民相沟通,所以能坦然地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与他人分享。可是,在孔子看来,这远不够,一个真正的仁爱之人,视天下人皆与己一体,而非仅仅是一国之内的人,所以,要拥有“人遗之,人拾之,又何必寻”这样的观念,如此,便把己之有亦视为他所有,自我的一切都可与他人分享,如此还有何割舍不下的呢?
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仁爱之心、慈悲之意者,把所赚之财大多回馈社会大众,这正是沟通了“己”与“他”之故。因此人们在临终时也就自然会减轻失落的恐惧,因为不会产生对财产难舍难分引发的痛苦。当然,也有很多人,把己与他分得一清二楚,绝不愿将己拥有的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于是,生前是个辛苦的聚财奴、守财奴;临终前则成为盯着自己的财富唉声叹气、难分难舍、心如刀割的可怜人。因此,人们要学会扩充心胸之法,消解分离的观念,去求得与他人、人类,乃至宇宙融成一片,建构如此人生观者,方能拥有真正幸福的人生。
可见,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死观,乃建立在由“死”观“生”的基础之上。人们生活中,多易于以“生”观“生”,以“生”(奋斗)求“生”(财富)。所以,很容易产生自己“一无所有”的悲叹、自怜。而面对“死”后真正的一无所有,人更陷入悲愤与伤心之中,如此造成生死两憾,生与死的品质皆不高的结果。所以,人们必须换一个立场,换一种视角,在“生”前便先行(意识上)到“死”(观念中),立于“死”的基点来观照生前。此时人们就可发现,无论你拥有的东西是多还是少,你都是个“富翁”,因为人之“死”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在此衬托下,你必能觉得自己拥有很多,而且会倍加珍惜你的一物一时,你所获得的爱情、友情、亲情,你所感受与能触摸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景,等等等等。此时,你决无生前“一无所有”的虚无感,有的只是“完全拥有”的充实感。而且到临终之时,你面对真正“一无所有”的结局,便会涌现出一种“感恩”之情,觉得我充实地拥有过,幸福地生活过,有那么多值得感恩的人和事,我何不心满意足?我何不安然地瞑目休息?我何惧何怕?这样由“死”观“生”的结果就使人们可以生死两无憾,生与死的品质皆高。
可见,要有健康的人生观,需由正确的死亡观为先导;而要拥有临终前的坦然、安详,人生观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当然也是生死学最重要的原则“生死互渗”所产生的奇妙作用。
三、“孤独”的害怕
人一出生,就是社会的,其生命的萌发、孕育,要靠父精母血;其成长、发育,要靠家庭养护;其工作与人生,要靠社会环境,等等。人,说到底,是一个人际与社会关系的存在,离开了这些关系的网络,人也许一天都活不下去。
由是,人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处于种种关系之中:晨起早餐,你便与农民与食品工厂的工人、商店等发生着关系;你与人聊天,便与亲人、朋友,或陌生人发生着关系;你工作,就与上司、同事发生着关系;你休闲,就与家人亲属等发生关系,等等。从这一层面来看,关系不仅是人生活的内容,简直可以说就是人生命本身。
实际上,人生的全过程是一刻也离不开关系的,人依赖于各种关系生存,也依赖各种关系而发展。虽然,有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在其作品中赞美“孤独”,认为离群索居、独自冥思是一种很好、甚至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此言谬矣。一方面,只要他有生命、要生活、在思考,就决不是纯粹的孤独,他还是与他人、社会、历史、传统发生着或近或远、或紧或松的关系;另一方面,长期的幽闭式独居,必给人身心带来极大的摧残,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监狱对囚犯最大的惩罚不是苦役,而是独个儿禁闭的原因所在。
人际的社会的各种关系,形成了包围于人四周的亲情、友情、人情、社会之情,人必须拥有这些“情”,才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人际的温暖、社会的温暖,才能体验到人生的美好与幸福;而如果人们拥有的这些情很淡很弱,一般而言,人们会感到孤独的痛苦,感受不到亲人、社会、人际间的温暖,此时的人生过程对人而言,成了一大冰窟,冰冷刺骨,使人生毫无乐趣与幸福可言。
关系、情谊对人生与生命既然如此重要,孤独、冷落对人的生活是如此的可怕,那么,延伸一步,死亡对人又意味着什么?
“死”对人而言,不仅是所拥有的物质性财富的全部丧失,更意味着人所有亲属的、人际的、社会的等等一切关系的丧失。生活当中很难忍受的孤独无助,也许是人死后必须承受的悲惨状态,这是许多人的想法。特别是自古及今,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最最令人伤心落泪的还是生离死别的场景。
“生离”,意味着亲人或朋友今生今世永无再见之日;“死别”则意味着生者与死者永远隔绝,不复相见。这种痛彻心肺、悲呛绝望之感觉,身临其境者固然冷暖自知;而耳闻目睹者又何尝不心有戚戚焉!
所以,人类对死的害怕,实际上就是对死给人带来的“分离”的恐惧。赵可式博士对临终病人的调查及研究说明,人对死亡感到害怕,其原因之一是“分离的恐惧”。她写道:“这种恐惧与人的个性有关,如果是非常想要抓住什么的人,非常粘的人、舍不得的人,对所珍惜的东西,舍不得放掉;尤其是对人,舍不得离开,分离的恐惧会更大。因为死亡是一刀两断,在人间所有舍不得的、依附的、依恋的人和事物,全部都要割断。从依附到分离,对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恐惧。”(参见《台湾安宁疗护之现状系列讲座一》,《安宁照顾会讯》第24期)
正如前述,各种关系的系统实际上就是人之生命存在本身和人之生活的主要内含,所以,死亡造成的分离让人如此害怕和恐惧。临终前人们恋恋相依、割舍不下的情景往往是最让人感动不已的;而临终的人与眼睁睁目睹着亲人生命正在逝去者二方面内心的痛苦又岂是语言所能表达其万中之一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试想世上何人能够免于此劫?
要消解人临终前对分离的恐惧,提升临终者的生存品质,关键在使其相信“人死后并非什么都不存在”的观念。当然,这一观念的建构应该放在人活着的过程中,而若仅仅在临终前才想到拥有这种观念,也许已经晚矣。
当人清楚地了解到,即便自己逝去,自己的事业还是可以长存、友谊可以长存、亲人能够一代一代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在人生活过程中,就应该万分珍惜这些不朽的事物,努力奋斗以求事业的成功;消解不正确的想法与做法,改善和加强人际间的关系,构筑一个暖意融融的家庭。到那死时,在亲人、朋友的簇拥下,在亲情、友情、人际之情的包围中,又如何不能安然瞑目?反之,一个人如果觉得人死就意味着一切关系的毁灭不存,那么必然会在生前就不在乎友情、社会之情,乃至于亲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会随心所欲,将他人作为手段以满足自我之欲,将社会视为攫取的场所而从不付出,如此生死观,必造成其生前人生道路的坎坷(因为少有人帮助他),以及死时的孤苦伶仃(因为没人愿意陪伴他)。这样,人生的痛苦与死亡恐惧交相作用,生与死皆无品质可言。
此外,一切神秘主义的文化传统与宗教,皆提供给人类某种死后世界存在的信息。人们可以通过中国民间的死亡观,看到“阴间”与“阳间”虽然隔绝,但“交通”很方便,阳间亲人供奉的祭品,阴间的“人”可以享受;阳间亲人焚化的“冥钱”,“阴间”之人也能使用;而阴间的亲属亦可显“灵”,显“神通”,帮助阳间的亲人避灾免祸、发家致富等等。由此可见,人间的亲情、友情、社会之情皆永恒不灭,持续长久,关键在你此生此世的作为,你如何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你是否巩固了亲情,赢得了友谊,改善了社会的关系,等等,从而在自己逝后人们仍然能长久地记着“你”,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以求的东西。当然,人们还可通过佛教的指引,明白人死后有二种可能:一是通过“死”的中介,轮回于另一世界;一是通过“涅槃”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死后的状态实际上都把问题弹回了人们生前所作所为的性质与内容。如果你觉得生前已尽心尽力了,“死”时何能不安心?因为我能够通过“死”“往生”到更好更无痛苦的世界,又为何不能坦然地步入“归途”?
总之,一个人只要生前与他人“不离分”,“死”时也就会“不分离”,而且,死后也能“不分离”,以至于永恒地“不分离”。
四、“形貌”的恐惧
小时候,笔者与家人同迁至农村,那真是百样的希奇,万般的新鲜。不久便发现,每个村子的后面,必有一公共坟场,内树木茂盛,杂草丛生,一堆堆黄土,便是天下生灵的归宿了。后又听老人们讲了许许多多鬼的故事,说人死时是多么的痛苦,形貌是多么的吓人,死后变成之鬼又是怎样的为害或为福人间。每当听完这些狰狞恐怖的故事后,我们一大群孩子伴着天上一闪一闪的神秘星星,就着清幽幽的冷冷月光返家,走着走着,我们个个心中发毛。
深夜的乡村,不时有犬吠声、不知名的虫子鸟儿怪怪的声响,就在大家心情紧张的时刻,崐不知是谁,大喊一声:“鬼来了!──”呀,大伙心中猛然一惊,不约而同地拔脚狂奔,越跑人越少,最后只剩我一人奔到家,脚也不洗脸也不擦,直躲进被窝,扯过被子将全身盖得严严实实,胸中的心兀自在扑扑乱跳。可是,到了第二天,众人似乎又忘记了昨日的恐怖,不约而同地在晚饭后再齐聚到专讲鬼故事的老人家中,围坐一圈,就着微微火光,听开了死人啦、鬼呀神呀的故事。听到最后,圈子越缩越小,大伙挤成了一团,以从彼此的生气中寻到抵御恐怖的透心凉意。
中国普通百姓,所受的死亡教育也许大多像我这般是从长者的故事开始的。当然,现代传媒越来越发达,人们通过书刊杂志、影像制品、信息高速公路等等,获得有关死亡的许多知识。尽管现在获得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先进,但关于死亡的具体内容还是与从前差不多,比如:死是非常恐怖的,死时人们两眼一翻、双脚一蹬,呜呼哀哉;或者疼痛异常,脸部僵硬,全身扭曲,双眼睁得异常之大,死不瞑目;至于人的非正常死亡,如夭折、自杀、灾害事故等,那就更可怕了,等等等等。这些有关死亡的信息一旦在人们脑海中扎根,便终身难以忘怀,而真的到了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知识和印象一齐袭上心头,造成自我恐惧万分,心情难以平静。
赵可式博士写道:“我曾经照顾一个病人,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半,我看他脑筋很清楚,情绪却不安,皱着眉头,于是我问他:‘你好像很不安,愿不愿意谈谈你的想法和心情?’他说:‘我很害怕,人在断气的时候,是不是两腿一蹬,脑袋一歪,就咚咚咚了?’”赵博士分析道:“他对死亡形貌的了解是从电视媒体来的,他害怕死亡的过程会不会很挣扎,是不是很痛苦,尤其是已经有痛苦的人,他害怕:‘我现在已经很痛了,那么再下去,到断气的时候,是不是会痛到无法忍受?’”
赵博士还指出,临终者对死亡过程也是非常恐惧的:“有一位得了癌症的三十多岁年轻太太,她跟我说:‘我生孩子的时候,在产房里叫得像杀猪一样。我的颜面尽失,觉得很丢脸,以后再也不好意思去看那位医生了。’她跟我说她的恐惧是:‘我断气的时候,会不会叫得比生产的时候再大声,或者比生产的时候更痛?’现在会喘的病人则恐惧:‘我断气的时候会不会像上吊一样,一口气蹩不住,脸色发紫,舌头伸出来?’这种种恐惧都是病人告诉我的,这些多半是要建立很深的关系之后,他觉得你不会笑他,才会表达出来。如果她与你关系不好,或者他不认为你能回答的话,他是不会表露的,你也不知道他恐惧什么。尤其是现在已经在受苦的病人,他更觉得死亡过程很可怕:‘我会不会一点一滴地断不了气?最后断气的形象如何?我的感受是什么?面貌身体是什么样子?’他会对此感到焦虑及害怕。”(参见《台湾安宁疗护之现况系列讲座之一》,文载《安宁照顾会讯》1997年第24期)
对临死前形貌及过程的恐惧,也许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的,从深层次看,它是与尸体的腐烂、骷髅的恐怖,死后世界的无法知晓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现实世界中也许并没有真正地看到或摸到这些东西,但从恐怖影视、小说、故事中早就对此刻下了深深的印象,所以,在临终前一想到自己平时万分珍惜的容貌身体将不可避免地肉销骨朽,而且临死前那喘不过气的难受和意识的模糊、疼痛等,又怎不使人害怕万分,痛苦难受?
为安抚临终者的心灵,一方面,现代科技应大力推进临终医学的研究,尤其是疼痛控制的技术,使任何疾病患者在临终前都能够基本上消除肉体上的疼痛。其次,则应该在社会上广泛地推行死亡教育,使民众不至于完全受追求轰动效应的影视和小说的影响,认识到在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人死前的痛苦是很小的,关键是自我精神与心理是否能放松和灵魂能否安详。实际上,一个人心理上的恐怖、灵魂上的不安必引发肉体之痛和全身的不适,这就加重了临终前的痛苦;而当自己心理平静,灵魂又有所归依,就可大大减轻肉体的疼痛,从而在身、心、灵皆安稳的状态下步入永恒的静息之乡。
可见,在消除人们对临死前形貌及过程的恐惧方面,观念的转变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疼痛控制的技术总是会日新月异、不断有所进步的,但人的观念变更则是一个困难的漫长过程,尤其是人们的心理定势,更是难以在短时期内加以改变。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加大全民性死亡教育力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我们每个人皆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因为那时我们世事未知、处于完全蒙昧的状态;而我们每个人却不应该也哭泣着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个人通过漫长的人生岁月都拥有了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有了理智与信念,有了文化与知识。所以,我们要学会在人生过程之中就去努力地透视死亡现象,悟解死亡的方方面面,为死亡的必至做好生理、心理与灵魂的准备,从而最终以坦然、甚至欣然的态度就死。
(文/心灵花园 )
下一篇:情绪管理:焦点疗法的本质 上一篇:心理学堂:如何掌控自我怀疑?
